敬请浏览其他论题
桥牌随笔——我的桥牌感受
作者:黄烨
在桥牌圈里跌打滚爬大概有十几年了,在十七岁到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想以桥牌为职业,但基于一些更现实的想法,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无论是什么时候,总是放不下桥牌。曾经有若干次下决心再也不打桥牌了,而每一次最后都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最终,总算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这辈子无法真正地忘记桥牌。在长达十多年的桥牌生涯中,自己觉得有着太多的感慨,桥牌,给我带来的是快乐、兴奋、沮丧、愤怒、伤心等多种不同而又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感觉。
我想以几件事来作为几种感觉的代表,表达我对桥牌的这种说不清的感觉。
一 沮丧
1993年6月,新加坡。首次代表中国青年队出征远东锦标赛,当时的中青队阵容鼎盛,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届国青队。的确,当时队里有石正均、石淼、王为民、庄则军、张邦祥和我,绝对属于豪华阵容。参加远东赛拿第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桥牌比赛不相信必然,那一次我们位于澳大利亚和中国台北之后,仅仅取得第3名。在我和张邦祥上场的时间里,我们丢了8个满贯,却没有叫到并打成一副满贯。在对澳大利亚队的关键性比赛中,我们必须大胜,因为我们已经落后了大约20VP。而比赛开始的几副牌我们确实看到了希望,有大约34IMP的先手,然而,顽强的澳大利亚人开始了他们的反攻,他们叫进了一个很不好的有局方满贯,但是分布太有利了,做成扳回13IMP;紧接着他们又叫到了一副满贯,叫牌过程大概如下:
北 东 南 西
1NT / 2NT /
3C / 4C /
5C / 6C /
/ //
你坐东,手持:S:9 8 6 H:K 8 7 6 5 4 D:K 9 3 C:2,首攻什么?
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作出选择的首攻。当时坐东的是张邦祥,最终选择了红心首攻,结果对手做成6C,但是我有DA,首攻方块立刻就宕。事后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很少就桥牌问题与人争吵,但那次是个例外。这副牌成了那场比赛的转折点,在后面的比赛中,我们又失误了一副大牌,这场比赛最后我们小负对手,我们并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缩小与领先者之间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我们彻底失去了争夺冠军的资格。刚到新加坡时的雄心壮志,转眼间就化为泡影,就象阿根廷队在韩日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时队员的反应一样,中青队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只有两个字:沮丧!!!!
二 愤怒
1994年,新西兰惠灵顿。在那一届远东锦标赛上,我们开始很顺,第一循环结束,我们领先第二名20多VP,形势很好,但第二循环开始后,新西兰队渐渐追了上来。我们最后两轮是对中国台北和澳大利亚,但比新西兰队只多19VP,而新西兰队最后两场的对手相对较弱,东道主完全有可能全拿50VP。由于前面我和庄则军一直没有休息,对台北队这场我们便和欧以红(当时台湾最优秀的年青牌手)做了个交易(注:这当然是开玩笑,就体育比赛做交易是违背体育道德的),他和他的搭档不上,我和庄则军也休息。我在房间里休息了一会,然后走到转播大厅,直播的是中国国家男队的一场关键比赛,我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每当中国队出现失误时,现场所有的老外竟然齐声鼓掌,这难道就是他们鼓吹的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我真的非常愤怒,我回到房间,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庄则军,我们两人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这帮老外失望一次。最后一场比赛开始了,由于上一场13:17负于中国台北,我们要拿到18VP才能确保冠军,而开局对我们并不好,运气也差,然后,正如第二天公报上所说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中国青年队在随后的8副牌中赢了79IMP”,最后我们以23:7战胜澳大利亚夺冠,让那些老外目瞪口呆。我想,如果我没有看到那幅场景,可能未必能承受当时巨大的压力,也许结果就会两样。这种力量或许就是愤怒的力量吧。
三 兴奋
1995年4月,杭州。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安徽参加全国甲级赛,那年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阵容不是很整齐,名次也一直在8~10名之间,最终是第8名,当然在1/4决赛中,如果不是有人摆错了牌礅以至于采取了一个确保宕牌而不可能打成的坐庄路线,我们早进前四了,没准还拿冠军了。我兴奋不是因为打破了安徽队四年降一次级的怪圈,而是下面的这副牌:叫牌过程很简单:
北 东 南 西
1H
X 3D 4S /
/ //
S Q 10 8 5
H 6 5
D A J 6 4
C A J 5
S A 9 7 4
H K 10 4 2
D 3
C K 7 6 4
西首攻D2,如何坐庄?这肯定是一副比较难做的庄。我当时确实也有思考的停顿,如果1秒种不到也算停顿的话。我用明手的DA停住,马上打方块回来,用S9王吃,西家垫红心。我不停顿地出S4,西家长考后出K,再出黑桃,我从明手出Q,击落东家的J,将吃方块回手,飞梅花,然后清将牌,用第四张梅花拖入西家,再吃一礅HK完成定约。不算很精彩但是很干脆,是吗?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事后有人问我:“你那副牌怎么打得那么快?你怎么知道SJ在东家?”我瞪大了眼睛惊奇地看着他说:“你书看得太少了,这是书上的牌例,天知道这计算机发牌怎么会发出书上的牌,这牌例我第一次看到想了很长时间,后来记住了,所以就不想了。”问话的人满脸都是惊佩之情。“哇!你运气真好,是哪本书啊?我也去看看。”我当时确实记不清是哪一本书。回家后,我翻遍了所有的桥牌书,竟然没有找到这个牌例?!这书不会是我梦里看的吧,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四 快乐
1990年5月的某一个晚上,南京大学校内宿舍。我很悠闲地躺在床上,幻想着要即将参加的全国等级赛。从1990年起,计划单列市可以组队参加全国比赛,南京市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南京大学。我们少年班队在刚刚结束的南京市甲级赛中获得亚军,因而有一对牌手的名额,学校初步定了由我和金士参加。要知道当时的我是多么的心高气傲,我总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的贝拉东纳,而金士可以成为葛罗素。我估计我将是最年青的参赛者。这时,一个同学走了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维。他也是我们班桥牌队的,按照我的评价,他可以继我和金士之后排到第3,也是一个准备把整个人奉献给桥牌事业的人。过了很长时间,他开口了,他说:“黄烨,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我突然明白了他想说的事。其实,四年同寝室的同学,有很多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我明白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口,因为他开不了口,因为参加全国比赛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沉默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我的心乱如麻。最后,我开口打破了沉默。我说,“明天我去和校方说,我要写毕业论文走不开,你代替我去。”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但我只知道,我回到安徽后肯定还有机会,但这肯定是他唯一的机会。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快乐,我学会了忍让,一种比桥牌中的忍让更高明的战术。
五 伤心
在我的早期桥牌生涯中,总体是比较顺的,20岁打安徽省队,21岁进国家青年队(这一纪录可能至今无人能破),两届远东锦标赛青年组冠军,两次世青赛第六,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抵消后来桥牌带给我的伤心。
我是一个没有多少上进心的人,对个人的名利追求不高,在经历了一些失败以后,我也明白,自己成为不了顶尖高手,平凡的天赋和性格上的弱点限制了我的进步。因此,在1996年安徽队终于没有保住甲级队后,失望的我远离了桥牌。尽管我每年大约还打一次比赛,但是我的心已经冷了。我选择了较为现实的人生,把精力放在了我的本职工作上,平时周六的训练我也基本不去,在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受到了好评,我也渐渐忘记了在桥牌上的雄心。
而在此期间,安徽队又从乙级降到了丙级,虽然第二年升级,但随后又降回丙级,开始了几年的沉沦。随着人事变迁,原来的老省队队员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安徽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支让人胆战心惊的安徽狂飙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支相对年轻、缺乏比赛经验的队伍。让人伤心的安徽桥牌!
此时,已经成家立业的我在做什么?似乎已经不热爱桥牌的我却在承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我是安徽桥牌造就的产物,然而在安徽桥牌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离开当了逃兵。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安徽队的队员训练和比赛时经常还要自己贴一些钱,然而他们都坚持了下来,他们凭的是对桥牌艺术的无比热爱和狂热追求,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为安徽桥牌保留一口元气。与他们相比,我真是太可耻了!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而不要管他们是否真正代表安徽队出战过:
朱晓源、张华藻、季军、胡朝晖、顾学军、朱元、李正、李文元、张道宏、刘向农、詹春晓、夏应祥
另外,有两个名字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文公皊老师和赵爱华老师。如果不是文老师,可能安徽队已经不存在了,这几年,是他承担了安徽队参加了全国比赛的费用;如果没有赵老师,合肥现在可能也没有几个人打牌了,省队也少了一个很好的练牌的对手。
……
终于,我回来了。尽管有很多阻力,我还是回到了桥牌圈。很幸运,我们今年升入了乙级。安徽桥牌的春天会来到吗?记住这段伤心的历史,抛开所有的恩怨,去努力创造未来,这是我的心声,也是全体安徽桥牌人的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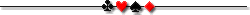
说明:本栏文章见仁见智仅供参考,凡未能确定其原创作者时均不予注明出处,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