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浏览其他论题
巴里.克兰和巴里.克兰大师分竞赛
巴里.克兰是有史以来最佳双人赛牌手,也是我在桥牌圈子里见到的最华而不实的人。负的方面,他是很糟糕的搭档:多变,卑鄙,自恋,报复心强,尖酸刻薄。他自己也这样描述他自己(除了自恋外)。正的方面,他对桥牌有好处。他在桥牌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是桥界内外知名人士(他曾是好莱坞制片人,以电视节目MISSION IMPOSSIBLE 和MANNIX 出名)。他有强烈的神秘感,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很有趣,是持续不断的闲话和“战争故事”的对象(他喜欢这样)。他在1995被冷酷
地谋杀,到今天仍然是一件迷案,从悲剧的角度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巴里热爱迈金尼竞赛(译注:年度美国大师分赛,在巴里死后,命名为巴里.克兰杯),热衷于成为竞赛的一部分。如果他自己不想赢得竞赛的话,他也热衷于决定谁能赢,而且通常他都能成功。有三个原因:1. 他是位伟大的牌手,大多数年份,每星期他都努力工作,按期或提前完成制片,因为他驱使他手下发疯似地工作,以便周末他能有时间打桥牌,然后他就会和那个他决定要赢得迈金尼竞赛的人一起打牌。2. 他在桥牌圈子里有很多重要的关系,说到关系,我是指另外的桥牌高手,重要的赞助人,以及美国桥联。3. 也许是最重要的,他很有钱。他从一个富裕的家庭出生,他自己在好莱坞也挣了很多钱。因此他决定不打职业赛(译注:指参加有赞助人组织的队),除非在没有更强的队的时候。他的搭档和队友都是很棒或者伟大的牌手。因为职业牌手需要糊口,我们没法象他那样长年和不需赞助人的队伍参赛。你也可以想像,很多伟大的牌手也没法象他那样。
巴里希望竞赛激烈,也尽力让竞赛激烈,这样会使他在那一年更激动,更快乐。坦白地讲,这也会让我们这些人更快乐,更激动,不管你是否直接参与了。也意味着,巴里让他的迈金尼竞赛的对手以及对手的支持者们怨恨。这让我在1984年的竞赛中得到了好处,那一年,我直接参与和巴里的竞争,好多伟大的牌手都支持我,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他了。三年来,我一直想找巴里的正面故事,但是一个也找不出。所以我就选了一些我直接得知的故事。
巴里是搭档杀手。在1985年春季夏威夷全国赛中,巴里和迈克.帕赛尔在公开双人赛中搭档,在最后一节中,他们打得非常棒,轻松地赢了冠军,这也是巴里在这项比赛中的无数次胜利之一(他在不是专家级的竞赛中,特别拿手)。迈克是我的朋友,比赛后我向他表示祝贺。迈克说,“我和巴里每年打一次,只是为了提醒我,我是多么仇恨和他打牌”。
杰夫.迈克斯特罗斯做得更绝。他和巴里搭档打了一场两节的区域性比赛,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和“迈金尼先生”至少打一次看看。比赛完后,杰夫把他们的约定卡撕得粉碎,扔给巴里,表明决不和巴里再打牌了。
在1983年萨可勒门托区域性比赛中,我和巴里搭档。巴里有一些很迷信的规则,他自己一直都遵守,他的搭档最好也遵守那些规则,否则他会很恼怒。规则之一就是,你要飞Q,两边都能飞的话,你不需要想,低花Q总是在J后面,高花Q总是在J前面。因此,假设你有AXXX,明手有KJ109,高花的话,你应该先拔A,然后飞J;低花的话,先拔K,然后出J飞。有副牌我和巴里叫到7NT,草花套在两手中正好是这样分布的。我有12墩牌,两手牌都是均型,我没指望能计算出对手的牌型。没问题,我想,既然没法算出对方的牌型,我就用巴里的规则,如果错了,至少他得闭嘴。我提了一些旁门赢墩,麻烦的是,对手牌型分配畸形,我能精确地知道左手家有3张草花,右手家2张,这样不用巴里的规则,能成功的机会提高了50%。同时,在楼下另一区的比赛中,迈克.斯冒伦也在打这副7NT,他也知道我和他同时在打这副牌。他也算到了对手牌型的精确分布,但是决定用巴里的规则。事实上,Q是在双张里,迈克做成了。迈克知道我会用技术上正确的打法,而不会管巴里的规则。他告诉他的搭档,“仔细听着,你马上会听到楼上的大吵大闹”。他对极了,我猜错了Q,巴里象吃了枪药似的,发疯的大喊大叫,然后跑出了房间。他回来后,故意把接下来的六副牌全部乱叫乱打(我们没能赢得比赛,只差0.5比赛分,他当然责怪我)。那天剩下的比赛中,巴里和我做了一些统计,看看他的规则是不是对,令我震惊的是,他的规则在六次出现的情况中,五次是对的。我告诉你,巴里是不可思议的。不管怎样,一直到今天,如果没有确定的线索怎么飞,我就遵从巴里的规则。
巴里死后,迈金尼竞赛改名为巴里.克兰最佳500赛,我们这些老家伙大多数还称它为迈金尼竞赛,部分是因为它好说出口,也因为习惯。同样,在巴里死后,才有了真正的迈金尼竞赛。有时,胜利者是不经意赢得的;有时,某个伟大的或非常棒的牌手决定要赢,而又没有其他人愿意投入金钱、时间、精力和他竞争,跟他作对;偶尔地,某个好手会决定要赢,并雇用职业牌手帮忙。
今年就很典型,容.安德生决定要赢,没人和他竞争。尽管如此,容不是巴里,他不富有,在大多数的比赛里,还得打职业赛。并且,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迈金尼竞赛通常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伟大的职业大师能够得到很多工作(译注:指有好多赞助人找他打牌),而且战绩不错的话,能够打败他。今年,杰夫.迈克斯特罗斯情况不错,非常可能会给容严肃的挑战。但我想这不会发生。
在杰夫刚开始打职业赛的时候,容给了他最大的帮助。杰夫欠他人情,所以我想杰夫不会故意挡道。杰夫打得好极了,队友和搭档都很伟大,他可能会不小心赢得竞赛,但我肯定他会试着避免的。杰夫一直都是为了赢,但是当两个人很接近的时候,我猜杰夫会放弃一些他通常都要参加的比赛。只要容能保持相对的健康,他应该能赢的。
下一年也会是很典型的一年,林.迪亚斯决定她想赢。林是世界上伟大的牌手之一,又很讨人喜欢,就我所知,没人会和她竞争的。如有人和她竞争,我会很吃惊的。所以看着吧,容今年(1996)会赢,林1997年会赢。
1983年上半年迈金尼竞赛
1983年,林达.皮特森决定她要赢得那一年的竞赛。时不时的,她需要雇用一些职业牌手帮她赢,容.安德生也想成为那些职业牌手之一。虽然在当时和现在,在他们之间并没伤和气,但林达告诉容她不想和他打。因此,容决定要和林达竞争,他自己去赢迈金尼。林达的主要支持者(很自然的)是即将成为她丈夫的保罗.刘易斯。那时,林达并不特别招人喜欢,保罗倒一直是桥牌圈子里的大好人,大部分林达的支持者们都是对保罗忠诚的人。
容的主要支持来自巴里.克兰。当时,容和巴里都不特招人喜欢,他们的支持者中,大部分是一些老朋友,招回了一些老家伙以及发展了一些新伙伴。
这是一场激烈的竞赛,大部分我知道的人并不在乎谁赢谁输,但是,每个人都对能有这场竞赛,并且参加者要进行殊死搏斗而感到高兴,竞赛肯定是激动人心的。林达一开始就领先,等到六月份萨克勒门托区域赛时,她已经领先很多了。
同时,我的情况
在七年没打牌后,1983年3月我决定重新认真打牌。我以前的桥牌生涯是作为一个盘式职业牌手,现在我决定要成为复式职业牌手。要成为成功的复式职业牌手,我需要证明我能赢很多大师分。
毫无疑问的,巴里是大师分世界里呼风唤雨的人物。我和他交谈后(我知道他需要一个能忍受他的高手搭档),他说:“好的,这里是规则、现状以及对策”。
规则包括:不要安全打法,不要牺牲叫,不要打我持完美牌,Q低花时在J后面,高花时在J前面,等等等等。当然,我打算在牌桌上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而不会管什么规则。人们都知道,如果你打破了他的规则,但成功了,他会什么也不说。如果你打破了他的规则,但失败了,他会象受伤的鹰一样大喊大叫。巴里喜欢大喊大叫,我想部分是因为个性缺陷,部分是因为他喜欢让人们知道他是老板。
现状是,容和林达正在竞赛(以前我并不知道),巴里支持容。在队式赛时,我和巴里搭档,和容以及他的搭档组队。在双人赛时,如果容不在,我就和巴里搭档。
对策是,巴里将为我们找到职业队,我在队式赛得到的钱包含所有比赛的费用。如果巴里有空参加双人赛的话,我就必须和他搭档。这是巴里的标准操作程序,这样能保证他有好队,双人赛中有好搭档。
巴里,迈金尼竞赛以及职业牌手
巴里在职业桥牌圈子里,有着巨大的能量,大多数职业牌手都很怨恨这个事实。
理由一:他和许多重要的赞助人有良好的关系。巴里很富有,很少在打职业队时拿钱。当巴里想在地区性的职业队里打牌时,赞助人只需支付他的搭档,而不是巴里。这对赞助人来说很合算,两个职业牌手而只付一人钱。巴里让他在队式赛和双人赛里取胜的机会最大化,“取胜”是他唯一的成功标准。
理由二:巴里或多或少控制着谁能赢得迈金尼杯,如果某人想赢得迈金尼杯,又没得到他的同意,巴里的态度就是:“是吗?我就是要阻止你”,通常他都会成功。
萨克勒门托火山爆发
萨克勒门托区域赛里,星期天最后的瑞士队式赛是爆炸性的。我记不清谁是林达和保罗的队友,但我清楚地记得容和巴里是和保罗.索罗威组队的。
在最后一轮比赛前,巴里和容已经赢定了。即使在最后一轮他们被痛宰,他们也会赢。林达的队在争第二,但最后一轮他们不是和巴里的队打。立即有人猜测:“巴里和容会不会放水,让林达队的名次掉下去,以减少林达在这次比赛的大师分总数?”。
在最后一轮比赛前,巴里走出比赛大厅,要求裁判在他的牌桌上安排一个监督员,以保证他们不放水。裁判告诉巴里,保罗已经要求了一个监督员在他的牌桌上。
巴里震怒了,他冲回比赛大厅,找到保罗和林达,向他们大喊大叫,在月球上都能听到。所有人,包括他的哥哥,都围着他们三个,没人想漏听一句话。容根本没准备,大喊大叫一开始,他也想挤到前面,参与进去,虽然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让巴里发疯的。他被人群完全隔开了,根本参与不了,于是他就在人群后面喊:“他们向我们挑战了,巴里,他们向我们挑战了。”
值得一夸的是,保罗和林达保持镇定和尊严,没有答理(当巴里狂呼乱喊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答理他)。回想起来,他们一定认为巴里是个疯子,莫名其妙就发作了。
完全是个误会,要求监督员的那个保罗是保罗.所罗威,巴里的队友,而不是保罗.刘易斯。
最后一轮比赛没有高潮,巴里和容轻松地赢了。
这场吵骂很重要,它改变了力量对比。巴里来劲了,不光是在那个时刻,而是在当年剩下的时间里都来劲了。容感到当巴里来劲的时候,没人能打败他。他希望巴里一直都保持这种劲头,这也是为什么当巴里发怒的时候,他在那煽风点火。
不管怎样,容很兴奋。容有点小聪明,认真研究过巴里的心理,容也许是唯一能认识到巴里的吵骂对巴里有多大影响的人。
1984年迈金尼竞赛 - 一月
1983年下半年
1983年下半年的迈金尼竞赛几乎是没有高潮的。林达领先了前八个半月。七月一日时,林达领先165分。八月一日时,只领先65分。八月份时,林达在红鹿的区域赛上赢得了183分,我想这是一个纪录了。到八月底,林达大约领先120分。
到九月中旬托而萨区域赛后,容开始领先20分,从此一路领先,最终赢了大约250分。
1983年最后一天,我和巴里在雷诺打每牌输赢制的队式赛,队友是容.安德生和杰拉德.卡拉瓦里。容计算过,如果我们能赢得前三名,他将要打破年度3000分大关。我想今年是容的年,更特别的是,今天是容的日子。
下午比赛结束后,我们开始领先。在晚上的比赛,我和巴里打的极好,以为我们肯定能赢了。最后一副牌打完后,我们等了容和杰拉德好长时间。终于他们也打完了,容开始向我们走来。50英尺外,容就开始喊,“不要生气,巴里,我们打得很糟,不要生气,巴里”,他就这么一直嚷着。我很不理解,今天应该是他的日子。我们对照了分数,他们确实打得很糟糕。巴里又要发作了,很明显准备骂人,但他勉强地控制住了。容到计分台看了一下结果,我们第三,刚刚让容超过3000分。
容回到桌旁,谢了巴里,然后走到比赛厅出口,站在那里接受大家的祝贺,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今年结束了。
并没有结束,三天后得到消息,容不知怎么地算错了大师分总数,他总共赢得2994分,而不是3000分。3000分大关还没人打破,现在我决心打破它了。
背景
在开始这个故事前,我想说我喜欢巴里.克兰(不管我怎样,他怎样),我想念他,他的个性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最有魅力的。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双人赛专家,在双人赛桥牌里有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他为桥牌带来了好处,我认为,人们关于他的闲话和好奇,比当时所有其他美国牌手加起来都多,也比从那以后所有牌手加起来都多。读了这些故事后,你可能不相信我会喜欢他,但我确实喜欢他。好了,开始我们的故事吧。
1982年9月,露达.乌尔西和我开始认真地相互喜欢了。露达漂亮,光彩照人,工作刻苦且绝对忠诚,她也是伟大的女牌手之一。1983年1月日,我从旧金山地区搬到洛山矶,这样我和路达就可以住在一起了。因为我结过4次婚,我并不是好的结婚对象。
从桥牌的角度看,露达和我对彼此都带来好处。首先,从1976年起,我不再认真地打牌,现在我又开始打了。其次,露达只打二盖一,所以我对这个体系变得很熟悉了,现在是我首选体系。露达认为,我在她的桥牌方面,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我教了她很多桥牌上的东西。
另一方面,她说在遇到我的时候,她非常自信地认为,她“和世界上任何牌手一样好”。现在,她明白了她并不是“和世界上任何牌手一样好”,倒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这是件好事,没有人和世界上最好的牌手一样好,包括世界上最好牌手本人。
1984年
1984年1月1日。毫无疑问地,今年我将赢得迈金尼杯。什么都准备好了。露达和我退掉了所住的公寓,打所有家当都储存了起来。我们会一起参加各地的比赛,并尽量多打。巴里.克兰完全支持我,几乎每个周末巴里都要和我打,并且在不是周末的时候,只要他不在好莱坞制片,他也要和我打。我的真实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打破年度3000大师分大关的人,我很自信我能做到。露达和我希望今年能有很多乐趣,成为我们记忆中难忘的一年。
一月的第一周,奥兰多。巴里和我打了整整一星期,队友有迈克.阿尔伯特及玛丽.阿尔伯特。迈克是非常有天赋的牌手,唯一的主要缺陷是,
他有时会考虑过多去搜寻精彩打法。玛丽是很好的牌手,水平高且发挥稳定。我们赢了大约100大师分。看起来今年开头不错,其实不是。有两件事败了这周的兴,并为今年剩下的时间带来了恶兆。
第一件事发生在这周中间,巴里和我在打双人赛。有一副牌,巴里打4红桃,对手是两个女士。巴里开始时藏牌了,两墩牌过后,他又从他藏牌的花色打出了一张牌。坐在我右手的女士说:“巴里先生,你藏牌了”。巴里看了看他打的牌,说道:“是的,我藏牌了。嗯,继续打吧”。
这副牌打完后,巴里在计分条上记下了4红桃做成5。我右手边的女士说:“巴里先生,你藏牌了,你忘了扣去赢墩”。巴里说:“啊不,我什么都没忘,是你忘了叫裁判了。对不起,女士们,我就是这么打牌的”。
我惊呆了,完全愣住了,没法作出反应。那两个女士什么都没说,天知道她们怎么想。我想我在牌桌上做的最坏的事,就是没有在那时候我自己去招请裁判,不过我确实不知道,(作为明手),我是不是能够发言。巴里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他从来不会管别人怎么想的。
晚上,我和露达讨论了这件事,我说我再也不会容忍类似的事发生,再发生的话,我肯定和巴里撕破脸的。象往常一样,露达支持我,虽然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会失去巴里的支持,甚至于引起他的仇恨。
第二件事发生在星期天的瑞士队式赛中,我们队一输一平,我能够(也应该)挽救这两场比赛的。巴里象鬼似地对我大喊大叫。除了上一年巴里对我喊叫过外,还从没有人对待我这样,这也是我第一次被人这么侮辱。难以置信,难以置信我能忍受这个。大风暴就要来了。
第二周,我们到科罗拉多温泉比赛,同样的,巴里和我打了整整一星期。因为我比他打的明显地好多了,也因为我们几乎赢了120大师分,巴里表现不错。对于这次科罗拉多温泉之行,我记得两件事。一是寒冷的天气,再就是保罗.所罗威在巴里做庄时,做了聪明的防守,在一场淘汰赛中击败了我们。巴里将牌是QJ976,明手是A43。没有任何将吃的危险,问题是如何让将牌只失一墩。巴里打出Q,到2,3,8。接着巴里出J,以对付左手方K1052,更主要的,如果右手方是108双张的话,得一超墩。左手方示缺了,保罗第一轮是从K1085中出8的,现在保罗得到了两墩将牌,巴里打宕了铁成的定约。当然,巴里第二轮不该出J的(译注:应出小的),但那是个聪明的陷阱。巴里最容易上这种当了,因为他无论怎样,总想取得可能的每一墩。事实上,巴里的一条规则就是:“不要安全打法”。
第三周到墨西哥城,巴里这周休息。这是我第一次到墨西哥城,玩的开心极了。墨西哥牌手是好样的,没法全部表述。多年来,我到过几乎所有墨西哥的区域赛,但我最喜欢墨西哥城的比赛,因为其他地方的比赛没有足够的墨西哥牌手。这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打职业赛(译注:指有人出钱和他打,这样,他的搭档或队友水平并不总是好的)。我也第一次和迈克.帕赛尔搭了档,打了没几手牌,我就意识到迈克是世界上伟大牌手之一。我赢了大约80大师分,我开始想,要赢得迈金尼杯是很容易的事。
第四周到蒙特雷。巴里会在周末来,和我打星期五到星期天的比赛。这周的其余时间,我有职业赛要打。出乎意料的是,我星期一下午到蒙特雷时,巴里已经到了。“你好,巴里”,我说,“见到你很惊讶。在周末前,和谁打呀?”。“你”,他粗鲁地说。“巴里,你应该到周五才来的,周五前我都有比赛,我不能毁约的”。“是的,你能”,他粗暴地说。我已经对巴里容忍了一件不能容忍的事(在奥兰多),那件事,至少让我有了心理准备,我也想找个机会向他表明,我不会再忍受我认为不能容忍的事。我很不高兴地说,“巴里,我不会那么做的”。“那么好吧”,巴里说,“周五和周六的比赛我们继续打。上午的淘汰赛,我没有队,我们要一起打上午的淘汰赛。星期天我会在另一个队里打。然后我们再也不一起打了”。“好的”,我说。
上午淘汰赛决赛的上半场,巴里和我打得很好,实指望我们能领先。结果,我们倒落后30IMP。巴里发作了,对队友大喊大叫,并拒绝打下半场。下半场,巴里真的没打。没有奇迹发生,我们被人痛宰。同时,巴里在双人赛中打得也不好,一星期情绪都很糟。
星期五到了,巴里和我打了比赛。我记不清我们是不是赢了,可能没赢,因为我记得我们彼此没说一句话。星期六我们同样没说话,一直到晚上只剩4轮比赛的时候。我们打得非常好,肯定赢了,巴里的情绪也终于好起来了。“明天我们和谁打呀?”,他问我。“天哪,巴里,你告诉我明天我们不一起打的。我已经有队了,不知道能不能加你进去,要我去查查吗?”。“不”,巴里说,“不麻烦了,我会再找个队,或者回家”。
巴里对他的年龄特别神密。原因是,他感到如果人们认为他太老的话,在好莱坞就很难找到工作。年初,他告诉我他开除了他的经纪人,那也是几个月来第四个。巴里在好莱坞不太好找工作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比以往更乖戾。同时,也意味着他有更多时间打桥牌了,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定要自己赢迈金尼杯。他需要找个理由来中止支持我的承诺。
在蒙特雷赛后,巴里说,一直到5月,他都有职业赛要打,但我们的竞争现在就开始了。对我来说没问题,5月份前,我也有职业赛要打。5月份后,我打算只有在有可能赢的情况下,才打职业赛。
如果我能打败巴里的话,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有我的优势。我已经领先了,而且有可能巴里会在好莱坞找到工作,这样有几个星期他就不能打了。事实上,那年有另外两个星期,他没法打牌。
另外,我比巴里年轻了几乎20岁。在1983年前,我一年最多打4到5个区域赛。1983年,我打了10个或15个。尽管如此,我曾没日没夜地打了15年盘式赛,几乎每星期都连续不睡觉地打好几天,我对我的毅力没有怀疑。就巴里来说,他还没有在一年里每星期都打牌的经历,他今年得这么做,否则他是没机会的。如果毅力成为一个因素的话,我就有非常大的优势。
不久,我发现我有另外一个优势。保罗.所罗威找到我,对我说我可以信赖他的支持以及大多数职业牌手的支持。我说那很好,我知道保罗是我的朋友,许多职业牌手和伟大牌手都是,我本指望得到他们中一些人的支持。“不”,保罗说,“事情要复杂的多。职业牌手们都烦透了让巴里来决定谁赢迈金尼杯。如果我的朋友想赢迈金尼杯,而巴里说‘是吗?那我就去赢,或者保证其他人赢!’,我怎么办?我们都希望你能打破巴里在迈金尼赛中的垄断,我们会帮你的。我会尽我所能,其他人也会的”。真是好消息!
和巴里竞赛,我的基本策略就是,尽可能地和巴里面对面地比赛。也就是说,和他参加同样的比赛,坐在不同方位。
巴里总是坐北(双人赛中,总是坐东),因为,正如迈克.琼斯指出的,“巴里想让人们都知道他才是老板,他想让他的名字排在前面”。
有机会的话,在队式赛中,我喜欢坐北。对我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有个队友喜欢坐北或者迷信的话,我总是让队友先挑。坐在北家的好处就是,你能正式控制牌桌上的气氛。如果我坐北的话,我希望在这桌的比赛能愉快,大家有礼貌,随意且效率高,不能让牌飞来飞去,不能让规则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等等。
如果在瑞士队式比赛时,一开始你是坐南北的话,你是不该再换坐东西的(就我所知,规则不允许你这么做)。不交换位置的理由是,如果你希望通过选择不同对手取得优势的话,对方也会要求这样的,结果是,比赛无限期推延,通常会造成双方有情绪。我见过多次这样的事发生了。
不管怎样,在1984年,只要巴里和我在一起比赛,队式赛中,我总是坐东或西。这样就保证了如果巴里的队和我们打的话,我和他就面对面,他不能通过抗议来逃避。
最后,我得把我以前短文中说的一些事再多说说。巴里是为迈金尼竞赛而活的,但除非他仇恨在胸,他是不能真正进入角色的。好手们,特别是加州的好手们都知道,我是个好人。但提醒你,我不是圣人。从性格上讲,我是那种母亲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的那种人(并不是说我妈同意我的四次离婚,她当然没有)。说到底,巴里得费好大劲才能让我成为他的敌人,才能引起他的仇恨。反过来说,露达对待人不象我一样唯唯诺诺(只是不同性格而已,如果世界上多些露达,而少些格兰特的话,这世界就好多了),所以露达就成了巴里仇恨的目标。我在场时,巴里不敢对露达太恶劣,因为我当然不会容忍(谁会呢?)。两个月后,他试过一次,在某种程度上,我让他逃脱了。那是后话。
1984年迈金尼竞赛 - 二月到六月
一月到六月发生的4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四月的第一周在卫奇塔(手术),四月的第二周在雷丁(烟灰缸事件),五月的最后一周在菲尼克斯(挑战),六月的第一周在萨克勒门托(和解)。
手术
三月下旬,露达和我在洛山矶,没事可干(应该说我没事可干,露达总是在做事)。少有的一周,没有赛事。我头顶上出现一个小肿块,藏在头发下面,我也是在早上梳头时才发现的,因为梳子碰到它时,很疼。然后我就忘了它,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是那种一天只梳一次头的男人)。星期四早上,露达注意到了我在梳头时的表情,就问我怎么回事。我给她看了看。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到狄克.卡兹家打牌,狄克是医生,也是好朋友,露达说我们晚上问问狄克吧。
我当然完全忘了这事,露达当然记得。晚上打完牌,露达叫狄克给看看。狄克说需要作些检查,他会给我们打电话的。第二天一大早(我意思是把我叫醒了),狄克就打来电话,他说给我预约了另一个医生,一小时后见面。我去了,那医生把那东西给割了下来送去化验。我就忘了此事。
星期一早上,露达和我飞到了维多利亚,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来这里。1984年的维多利亚和今天的维多利亚一样,给人印象深刻。星期天晚上,狄克来电话了,“不要紧张,但是是坏消息”,他说,“你头上的肿块是癌。明天你去哪?”。“圣.迪艾哥”,我说。狄克说,“你到那后,一有空就给我打电话”。
在圣.迪艾哥的第一节比赛是淘汰赛,我打了我一辈子打过的最坏的一节比赛,就是不能忘了我有癌症这件事。这一节后,我给狄克去了电话,他给我约了一位医生。露达和我一起去见了医生,他把那东西割了下来。“我可能割的太多了”,他说,“但想保证全割了它”。“听起来不错”,我说。
两星期后,那肿块又长起来了,比以前的更大,更疼。直到周末,我才承认它又长起来了,因为我不想罗嗦,也不想错失比赛。我给狄克打了电话,下一场赛事在卫奇塔,他在那又给我约了个医生。
星期一,露达和我在卫奇塔见了那个医生。他说我应该回家,做手术,然后花三到四周时间恢复。我说,“医生,你不明白。我正在进行一场竞赛,要花整整一年时间,我不想输”。医生说,是我不明白,我的情况有生命危险,另外,他不打算给我手术。我说好吧,下周我会在雷丁,我会在那里找一个愿意做手术的医生。
这时,医生和露达交谈了一番,把我搁在一边。露达告诉医生,“确实是的,格兰特有点疯,他说到做到”。医生让步了,准备在第二天早上淘汰赛后立即给我动手术,打算让我能及时赶上下一场比赛。
我不知道我昏迷了多久,到医院后发生了什么,我根本就不记得了。我及时地赶上了下一场比赛。手术后第一天的双人赛,露达打的糟透了。
我终于忍不住了,把她拉到一边,说,“亲爱的,你怎么啦?你打的糟透了”。露达说,“格兰特,每次看你,我都怕你从椅子上掉下去,杀了你自己”。我说,“亲爱的,不要担心我,我没事”。我确实没事。
这次比赛好极了,我们赢了四个冠军,赢了143大师分,在当时,是我在所有比赛中赢得大师分最多的一次。
烟灰缸事件
1984年的时候,比赛中抽烟还是允许的。不久,美国桥联试了设立吸烟区和非吸烟区,再后来就全面禁烟了。巴里抽烟,我也抽烟。露达抽了多年的烟,但她在1976年戒了,到1984年,她开始对烟过敏了。在和露达打牌的时候,我不抽。但一有机会离开牌桌,我就去抽一颗。
在星期天瑞士赛打了五轮或六轮后,我到外面去抽烟。露达走来告诉我,轮次分配已经好了,我们下一轮和巴里队打。我说好的,我马上就去。巴里的桌旁还没人,露达在北家(巴里的位置)的两边各放了一把椅子,每把椅子上放了一个烟灰缸,这样,烟缸就不会放到桌子上了。
我到牌桌的时候,巴里和露达已经在那里了,巴里的搭档(我记得是容.安德生)还没到。巴里在抽烟,用一种他最令人不舒服(你只有看到,才会体会到)的姿势,从露达旁边的椅子上抓起烟缸,放到桌上,放到露达面前。露达问我是不是愿意和她交换位置,这样她就可以躲开那个烟缸了。我说当然可以。“啊不!”,巴里向露达讥笑着说,“你到哪,烟缸到哪”。
我恼火极了,把裁判叫到桌旁。此时,周围桌子上的牌手们都很好奇,想知道怎么回事。我向裁判解释了情况,他的回答是,“你们都是大人了,你们自己看怎么办”。裁判走开了,但没走多远,另一桌上一个家伙跳起来,一把抓住裁判,开始训斥那个裁判。我的意思是,那个家伙真地把那个裁判训斥得够呛 - “无脊梁骨,胆小鬼,水母”,等等等等。骂了一通后,那伙计回到自己的桌旁,大家热烈鼓掌。
我并不是为了给那个裁判在这件事中辩护,我和他认识了35年,这是他第一次做了我认为是完全错误(而且胆小)的事。很怪的是,虽然巴里自己是个胆小鬼,但他能让别人胆小。
说回来,在我们桌上,情绪很火爆,很敌对。巴里和露达都知道,我快要把巴里拖出去了。露达给了一个台阶,说:“我还能忍受,我们打牌吧”。整个比赛,巴里也还有自知之明,一直闭着他那鸟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把他们痛宰了。
挑战
五月的最后一星期是在菲尼克斯,也是巴里和我有职业赛的最后一周。周末,我和阿兰.科克打,他是一位有前途的牌手,现在已经多年没见他了。阿兰和我互相很喜欢,比巴里所知道的还要好。星期六的时候,巴里对阿兰说,“你为什么要和那家伙打?他什么都不能教你的”。阿兰听了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后的极限,巴里要还债了。
那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个非常长的挑战书。首先,我提出和巴里打10万元的赌,赌今年谁赢迈金尼杯。其次,我向巴里挑战,打一场特意安排的比赛,谁也不能退出,直到有一人赢到10万元为止。第三,我提出,让全国最好的100位牌手来选择今年迈金尼杯的胜者和特意安排的比赛胜者,每选对了一个,就得到1000元。如果他们选择我,并选对了,巴里得付他们1000元;如果他们选择巴里,并选对的话,我就付他们1000元。第四,我提出赌10万元,赌大多数前100位高手会选择我会赢得那两个竞赛。
这会公开羞辱巴里的,因为我知道(至少在我心里)我会赢得所有打赌,而且我肯定最好的牌手们会赌我赢。巴里知道我没有一分钱,但他知道我朋友很多,我会从他们那里筹到钱的。
在晚上赛后一小时左右,我找到这次比赛的主裁判蓓琪.罗杰斯(她后来退出美国桥联,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我把挑战书给她看了,请求她同意我第二天把它贴在赛场内。她问我下星期一会去哪,我说,“萨克勒门托”。她又问巴里会不会也去那里,我说是的。然后她说,她没意见,她同意我第二天把挑战书贴在菲尼克斯赛场,但她建议我等到萨克勒门托再说。那样,我可以在比赛开始时贴出去,轰动会更大。虽然蓓琪比我年轻,她聪明,我不是。但是我足够聪明到接受她的建议,我决定多等一天,等到下星期一在萨可勒门托再贴。
第二天,鲍比.沃尔夫问我是不是可以看看挑战书,我说当然可以。我回到房间,把挑战书给他。他读了挑战书后,还给我,说,“格兰特,我希望你把它贴出去,因为对桥牌来说非常好。但是,我不认为你应该贴出去,因为对你来说非常坏”。我说,“你意思是说我会和巴里成为永久敌人,他会报复我?”。“是的”,鲍比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谢了鲍比,说我不会害怕巴里。
在这,我先离题一会儿,因为鲍比和我的谈话虽然短,但非常重要。我认为鲍比和巴里,这两个桥界关键人物,洞察力非常强,非常有见地。
鲍比是有史以来非常伟大的牌手之一,他也贡献了他生命的大部分为桥牌服务,为桥牌发展服务。他曾是美国桥联主席,世界桥联主席,以及其它职务。那个响亮的“积极的道德标准”口号,可能就是他建立的,至少是他传播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对桥牌的发展贡献比鲍比更大。
就我所知,世界级牌手中,没人比他贡献大了。
我向巴里挑战会对桥牌发展非常有好处,会造成对桥牌的宣传,引起公众的兴趣,这正是鲍比想要的。但是他仍然劝我不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担心这对我个人和职业是灾难性的。他是个好人,不光是好人,他是有人性和聪明的人。
我和鲍比并不总是合得来,但除了我和这位朋友个性不同外,我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我和他有隔阂。我对政治完全不关心,所以我不知道,或者说并不关心鲍比(或任何其他人)在桥界的地位。但毫无疑问的,我知道鲍比是什么样的人。作为人来说,我尊敬鲍比。
鲍比所说的对他自己也有好处(虽然不是他的原意),也表明他很了解巴里。首先,巴里在桥界有巨大的能量,他能对那些靠职业桥牌维生的伟大牌手们,造成很大的伤害。其次,如果巴里被谁惹怒了的话,他会用他的能量去报复的。牌手们担心(害怕)的是,巴里会很恶毒地,甚至无来由地使用他的能量。
坦白地讲,那时我还不熟悉桥牌圈子,很天真,不能领会巴里能量到底有多大。我当然知道他在迈金尼竞赛中的能量,但又怎么样呢?说回来,我根本不介意。我把1984年当成一种探险,根本没打算要呆在桥牌圈子里,更不用说靠它过日子了,那是我后来才决定的。
和解
阿尔.埃文斯是个好伙计,非常风趣。比赛期间,他喜欢花时间在大厅和每个人聊天,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常在大厅遛达,他总是知道所有的闲话。阿尔和我是朋友,他和巴里也是30年的老朋友。在蒙特雷赛后,当巴里和我真正开始竞赛的时候,阿尔经常告诉巴里,说他支持我。我想,阿尔喜欢告诉巴里他支持我,因为阿尔感到他是唯一能对巴里当面说那些话,又不被惩罚的人(也许他是唯一能逃避惩罚的人)。
星期一下午,露达和我来到了萨克勒门托的旅馆。阿尔正坐在大厅里,对我说,“嘿,格兰特,有新消息吗?”。我说,“嘿,阿尔。有个有一些令人激动的消息。看看这个,我正准备把它贴到赛场去呢”。
阿尔扫了一遍挑战书,对我说,“格兰特,帮我个忙。把这个给我,一小时后我再和你谈”。当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巴里已经到了,阿尔准备把挑战书给巴里看看,但我并不关心。我信任阿尔,我说,“好的”。
一小时后,阿尔来到我们的房间。阿尔已经和巴里谈了,来给我们转达。巴里不想让我贴那个挑战书,如果我不贴的话,巴里发誓,在当面和背后,他都会对露达和我友好的。
我想,巴里能答应变得友好,他是在让步了。我非常想煞煞巴里的威风,我确信他应得那样的惩罚,我也有把握我能煞煞他的威风,很多人会很高兴看到他被惩罚的。
但是,露达非常想接受协议,阿尔也是,我并不那么介意。我的主要意图是,让巴里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对露达和我指手划脚,否则,我能够,也打算做些什么来对付他的。现在他知道了。
那年剩下的时间里,公开的敌对减少了,现在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到大师分上了。五个月过去了,还剩七个月,我领先300分。
1984年迈金尼竞赛 - 6月到结束
八月的第二周,露达和我(以及巴里)参加罗切斯特区域赛。露达和我在打一场双人赛,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家伙,毫无理由地,说了一些令人难听的话。露达很生气,正要反唇相讥,我给拦住了。我说,“放松些,亲爱的,显然这家伙是从纽约来的”。
那家伙说,“听者,为了今天是不是可以来打牌,昨天晚上我和老婆大吵了一场。昨晚我开车过来,路上车抛锚了,半夜里在路上等了几小时才有人帮我。到了这里,又到处找不到我的搭档。昨晚我一夜没睡,昨天是我渡过的最糟糕的一天。请原谅我,我不是从纽约来的,我是从蒙特利尔来的”。笑死我了,我爱这家伙。
我保持着大约300分的领先优势,一直到10月份,然后灾难降临了。
九月份第一周是劳动节区域赛的一周。这周全国有许多区域赛,最困难的就是在旧金山。因为自从1961年以来,我一直住在旧金山及附近地区,我想在那里打,这样我可以拜访一些朋友。巴里去了谢里夫港。我这周赢了大约25大师分,巴里在谢里夫港赢了大约100分。
接下去的一周是我事业中最坏的一周。在路易斯维尔,我只赢了大约15分,幸运的是,巴里只赢了40分左右。再下去一周在河床,巴里赢了130,我赢了80。另外,在一个没有区域赛的星期里,巴里在一些地方赛中比我也赢得多。
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区域赛从9月17日开始,我和最伟大的桥手中的两个搭了档。和保罗.所罗威在两个双人赛里搭档,和鲍比.列文在另两个双人赛里搭档,赢了四个第二。巴里和托米.桑德斯搭档,得了四个第一。有点沮丧,现在我只领先56分了。
1984年后,我有幸和托米打了不少牌,所以我清楚地知道,托米.桑德斯也是最伟大的牌手之一。他很魁梧,是个没废话的家伙。他是巴里唯一
尊敬的搭档,部分是由于托米的牌技高,但大部分是因为如果巴里侮辱他的话,托米会揍死他的。在巴里的搭档中,托米也是唯一能总是做他认为正确的事,而根本不管巴里规则的。
在杰克逊维尔,埃里克.罗德维尔和露达和我住在一起。埃里克有多方面的天赋,天赋之一就是模仿。比赛最后一天,埃里克模仿了容.安德生。容在楼下对桥牌迷们讲竞赛的事,说道“巴里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牌手,墙上有他的手迹”等等。埃里克模仿地好极了,我笑坏了,这是
我自从蒙特利尔那家伙后,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奇怪地,也许是愚笨地,我并不担心这场竞赛。部分是由于自信,部分是因为我相信世间有正义,虽然听起来怪怪的。不管怎样,我告诉露达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发生的话,最后几个月会更有趣的。
接下去一周,我到萨斯嘎顿,巴里去了托皮卡。我赢了85分,巴里赢了45分,然后我就开始了我事业中最大的连续大赢。在圣.迪艾哥全国赛前的四个区域赛中,拉斯.维加斯、苏斯瀑布、斯鲍肯、日内瓦湖,我在斯鲍肯赢了94分,在其它三个地方都赢了超过100分。
圣.迪艾哥全国赛的最后一天,露达、格罗佐、黎亚.杜邦(译注:格罗佐的老婆)和我赢了北美瑞士赛。那天结束后,露达和我都累了,我们回到房间,上了床。我突然意识到,这次全国赛,我赢了200分,现在是11月30号,我已经领先将近600分,只剩下一个月时间了。我刚刚超过3000分,竞赛结束了,我肯定赢了。为什么我们还在床上而不是去庆贺呢?露达让我冷静了下来,“因为明天我们要到帕萨地那去打区域赛”。
在帕萨地那,我赢了超过100分。巴里也在那里,忧郁,不高兴,疲倦不堪。今年只剩下两个区域赛了,我又犯了错误。就象伯尼.蔡曾指出的,我应该一鼓作气,赢尽可能多的大师分。相反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打了职业赛。
巴里在1984年赢得的大师分,比他在以往任何一年赢得的都要多300分,但结果是,我轻松地赢了迈金尼杯。帕萨地那后,巴里没再继续打,他取消了迈阿密和雷诺的比赛。
这一年里,我和超过160人搭过档或组过队,所以明显地,我没法把他们全列出来。大部分是我在1984年前认识的朋友,有些人我以前不认识,但到现在一直是朋友。
后记
1985年前两个月很怪,人人都以为巴里会打算赢1985年的迈金尼杯,但他完全没有露面。他前两个月一点没打,没人知道他在哪,在干什么。
终于他又开始打了,状态不错,虽然没和他最好搭档打,还是一直赢,
戴安.乔纳斯是巴里的最好朋友之一,那年春天,戴安告诉我为什么巴里消失了大约3个月。巴里曾告诉戴安,1984年的竞赛后,他是“一辈子中最压抑的”。显然地,他需要时间单独待着,准备重整旗鼓。
当巴里回来后,我不知道我和他的私人关系会怎样。令人吃惊的是,巴里非常有好,他邀请我去吃午饭,我们同意要再一起打牌,我很高兴。没有人愿意和巴里打太多,但偶尔打打还是不错的。和巴里一起打牌,是我所知道的最激动人心的。这样说也许是过分了些,毕竟我和皮特.平德搭档了多年。
凯丽.舒曼(现在是凯丽.山崩)是巴里的(以及其他任何人的)最好搭档之一,凯丽也是巴里的朋友。在一次(1982年?)世界杯混合双人赛中,巴里和凯丽赢了冠军,领先第二名有4副牌之多,难以置信的表演。凯丽也是我的朋友。
1985年7月上旬,洛山矶区域赛正进行到一半。在晚上的比赛后,巴里在家中被人残忍地谋杀了。第二天晚上,在消息得到官方证实后,凯丽和我去了一家酒吧,喝的太多,都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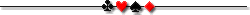
说明:本栏文章见仁见智仅供参考,凡未能确定其原创作者时均不予注明出处,敬请见谅。